“石家庄心理咨询机构”,“石家庄心理咨询中心”,“石家庄心理咨询”,“石家庄心理医生”,“石家庄心理”,“石家庄德中心理”,“石家庄心理实习”,“石家庄心理督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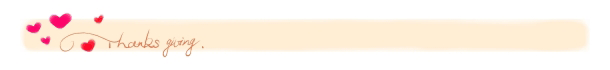
精神分析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处理移情(Dr. Klaus Kocher, Frankfurt)
在精神分析关系中的移情及其应用被看作是精神分析治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过去十年来,精神分析的移情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自恋或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也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能不能说在这些患者身上有通常的移情现象。而且,移情这个概念本身也处于争论之中。
对移情概念的经典看法认为它是过去的纯粹重复,正如Greenson所提出的这是一种落伍也是“时代的错误”,这种经典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对于许多精神分析师来说,由于对精神分析认识的拓展,移情也慢慢经历着变化:它从“一个人”的心理学转向了“两个人”的心理学,将治疗师角色本身卷入到更大的范围内,以更积极地方式将治疗师置于互动过程中。
尽管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发生着移情现象,但它仍然是精神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出现于治疗设置中的移情非常有助于理解患者的潜意识动力。
因此,精神分析师尽力去理解患者所谈论的东西在人际关系这个框架中所聚焦的内容。患者提到的一切都将分析师引向这个关注点,患者所说甚至没有说出来的一切也是不断地涉及精神分析关系中的隐含意义。精神分析师通过它尝试捕捉到患者的潜意识以及他所隐藏或展现出来的感受。
由此,精神分析中的一些情形如投射性认同、角色反应及精神分析师的互动部分扩大和丰富了移情这个概念。
1、我自己的分析工作中的实例
当精神分析师和患者间发生冲突时,移情现象最容易被看到。由于移情的这个特点,我想举一个我自己工作中的案例是十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移情的:
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在她生育第二个孩子后不久开始在我这里开始接受分析。她的丈夫是一个工程师,她自己是一位执业兽医。因为她在自己家中执业,所以她易于同时也非常成功地将自己的职业与家庭目标整合在一起。她们夫妇在外人眼中有着令人满意的私人生活和社交生活。
然而,在她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感到越来越受限制并且变得抑郁。她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地过自己的生活。曾经令人十分愉快的社交接触现在看起来是简单而肤浅的,而她现在的婚姻生活似乎也没有她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美满。她抱怨自己只是离家后迷失在婚姻中并且没有体验真正的生活和独立。她的丈夫尽力去理解她出现的危机,但看来他失败了而且很恼怒,这使得她很退缩。正如她所意识到的那样,她目前为止的生活正处于危险之中,并且危机更多地来自于她自身,因而她决定去见一个精神分析师。
我想简单描述一下我们的工作以使大家明白移情究竟是如何影响到分析性会面的。当来访者在经历了最初相当合作的阶段后她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默。我要描述的那次治疗是以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开始的:我因为交通堵塞而稍稍迟到了一会儿。她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长时间沉默开始了这次会晤,随后她开始谈东谈西,但是并非真正参与其中。她看上去很恼怒。我开始面质,问她生气是否因为我迟到这件事。“当然”她回答道:“但是,这不是你的错,是交通堵塞造成的”。我回答道:“是的,你说得没错。但是当你等候在治疗室门外时并不知道我今天迟到的原因。我很想知道当时你是怎么想的。”“是的,但这个真是太愚蠢了。”当我鼓励她将自己的幻想说出来时,她发现这么做非常困难。但之后我知道,她的幻想就是我更喜欢另一个男性来访者,那个来访者的治疗时间在她之前,她有时会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人。她认为我更喜欢和那个男性来访者在一起工作,并且我之所以接受她是因为没有其他男性候选对象。当她第一次在我们的工作中意识到自己的这些幻想时,她开始感到某种愤怒甚至是怨恨。我鼓励她说出更多的幻想,而后她承认她还有一个幻想,就是我之前是在和前面的来访者一起喝咖啡而后就是忘了她。
我说:“你之所以认为这个幻想很傻是因为你当然知道我不会和其他来访者一起喝咖啡?是否你对此越不知情,你就越会有这样念头?”
通过越来越多地谈论她的幻想,她变得能够克服自己的愤怒,嫉妒和羞愧。我们很久之前所讨论过的一些话题开始重现,但它们现在却是以一种和先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她生动的情感反应,使得这些内容变得鲜活且丰富多彩。
她开始谈论那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她小的时候很喜欢这个弟弟并且强烈地爱慕他。但现在她却回想起许多她弟弟与她父亲之间的记忆片断。她记得父亲曾经教自己滑雪,但是当弟弟大到也可以学滑雪时父亲就变得非常忽视她。她之后觉得自己就像第五个轮胎。到了晚上的睡觉时间,父亲会更多地照顾弟弟,会给弟弟讲很长的故事并且会和他开玩笑,然后仅仅是经过她的床很快地和她说声晚安就完了。她怨恨父亲和弟弟之间的这种亲昵并且觉得自己简直要被这种嫉妒给毁了。她一直对父亲掩藏着这些感受,当父亲由于工作不在家时她才会觉得松了口气,因为那时她可以暂时摆脱这些感受的影响。
现在,在与我的关系中,患者非常明显地重复了这种嫉妒冲突。她正幻想着一个婴儿期的、内化的冲突,在与我的关系中她从来没有真正地处理对她父亲的情感。移情总是一个潜意识幻想的现实化。
在分析过程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能掌控生活的、成熟的女性,而是一个感到被父亲深深忽视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渴望被爱和被欣赏的愿望被父亲深深地挫伤了。因此,她以怨恨来应对这种爱的受挫,又将嫉妒指向她弟弟,因为弟弟得到了那些她没有得到的东西,而且最终她对她的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母亲看来没有意识到所有的这一切,她母亲全然没有注意到而且没有帮助她处理这些感受。她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些,并且与自己的依赖作斗争。
尽管在之后的成年生活中她能很好地形成和处理关系,但她早年的冲突仍潜意识地持续着,直到出现导致她来治疗的危机时这些冲突又复活了。但她并不是就让这些冲突存在着,而是将它们带到了分析治疗中,并在治疗中通过移情来修通它们。
我们把移情看作是在目前的治疗关系中内化的婴儿体验的再现。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例子,如果婴儿的冲突再现,那么分析师不可避免地成为冲突中的一方,就好像目前实际的冲突是绝对真实的。如果这种移情的特点是带有诸如怨恨、嫉妒、羡慕或拒绝这些情感的,我们称之为“负性移情”。在负性移情中患者实施了一种行为,在现实关系如伴侣、朋友关系中通常是很难去处理的。如果分析师成功地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过去关系的病理性、冲突性再现,那么它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而且所有看似不恰当的感受会呈现出有意义的潜意识冲突。将患者的移情看作是过去关系的一种有意义表达,它会变成一种交流——而且如果分析师能够阐释这种交流,他能将移情转化为交流。
因此,患者试图通过移情来再现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他还不能通过语言来交流——甚至他不知道他想要交流什么东西。他不交流,因而他扮演。他不记得,他只是重复。
非常重要的是,移情现象并不是分析情境中的特定产物。其特别之处在于精神分析对移情的理解。所有的人类关系都是建立在原初关系的体验之上的,也是以移情为基础的。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将婴儿的关系转移到现实关系中。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新的体验。基于人类的这个普遍倾向,精神分析创造了其主要的治疗手段之一:移情及其导致的移情神经症,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移情是可以被修通的。
Freud将人类这种普遍的转移倾向称作为强迫性重复。他想要描述的这种特别的精神倾向,即在现实关系中重复和上演内心冲突的潜意识记忆模式。这些模式是潜意识的,但仍然动力性地活跃着。同时,它们不能在意识层面被加工处理,但趋向于在新的关系中不断被重复。所有的东西都一直会再次发生。
如果一个负性移情出现得很频繁,则治疗师起着某部分作用。那么就有必要去修通这个再现的冲突——Freud称之为阻抗——这是分析情境下移情的特征。
2、移情概念的历史概述
Freud很早就提出了移情这个概念,最早是在他的“癔症研究”一文中(1895年)。十年后,在他的“朵拉案例”中他进一步明确发展了他的理论,在这个案例中他观察到移情的作用及其治疗意义。他一开始认为是阻碍精神分析过程的东西——出现指向治疗师的感受和情感,后来被证实是治疗中一个非常有用和强有力的工具,通过它可以触及到患者正在处理的潜意识内容。
实际上,Freud没有能成功应对朵拉对他的移情,而是在他终止了对她的治疗后他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移情。
他开始区分过去的纯粹重复和对过去的修正两者之间的区别。对过去的修正与内在精神世界的改变过程有关,它会使个人的内心世界进一步发展。
之后,精神分析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它非常强调患者此时此地的情感。基于对“朵拉案例”的理解,Freud越来越相信通过分析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移情有可能直接观察到患者的潜意识愿望和冲突。
他进一步又将移情区分为正性移情和负性移情。各种感受,爱的情感和恨的情感被归为不同的移情反应丛。
他在早期时对移情的解释是驱力取向的:因为早期客体的内部表象潜意识地承载着力比多能量,通过潜意识地移情过程,这些能量被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
后来,许多精神分析师一致认为不仅本我的潜意识部分被转移了,而且超我的部分也被转移了。
客体关系理论进一步推动了此概念的发展,即认为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也是有移情倾向的。(?)
在分析情境下处理移情看来是一个多维度的主题,因为当你尽力想要去捕捉潜意识现象时势必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精神分析师的潜意识会卷入其中。
在极端的例子中被认为是移情的内容也可能主要是治疗师的防御——他的所谓反移情投射到了患者身上。
正如我之前已经提到的,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已经开始质疑移情是否仅仅是过去的重复或是一种经潜意识修正后过去事件的创新。你也可能质疑:是否分析师与患者关系中的任何东西都应该被看做是移情,或在这种关系中是否还有着其它“真实的”方面。
许多年来,移情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恰当的理解反应,它可追溯到患者的过去,而与目前真实的治疗关系无关。
一位在战后精神分析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治疗师Greenson将此称为“时代的错误,即由于过去的客体关系的重复而产生的时间上的错误”。
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更复杂了:有一群精神分析师仍然追随这种主流理论(这被称为保守派)。他们将分析师的地位明确定义为一个白屏(正如Freud所提出的),它只反映了患者的投射。
在这个模式中,分析师并没有真正扰动到患者。治疗师所理解的大部分东西看来是患者的(神经症性的)移情。除此之外,治疗关系中还有一个方面被排除在外,它就是工作联盟,它确保了现实中治疗关系的功能。
分析师的另一种地位被称为“根本地位”:他们认为进行上述区分没有任何用处。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提出移情不仅是来自于过去的现象,而且也或多或少受到现在的真实关系的影响。这引出一个主要的结果:即我们不能再说患者的现实世界仅仅是(神经症性的)移情,或是没有受到移情影响的纯粹的现实世界。从客体关系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混合的状态,分析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深深地卷入其中。
现在,精神分析师处理移情时并不只是将它看作一个仅仅由患者的神经症性理解造成的错误。正如Merton Gill在他80年代的重要著作中提出的,在分析过程的开始阶段就不得不考虑到移情并对其进行阐释,当在患者和治疗师的关系中出现移情时,需要在此时此地清晰地指出移情作用的重要性。
这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焦点的转变:当移情阐释聚焦于分析情境中的此时此地时,分析师无法再将自己限制于仅是镜子的经典地位,即只反映患者的幻想和情感。这使得在分析过程中不能仅仅分析过去和其它与治疗关系无关的材料。
Gill明确提出正是分析关系在现在形成了治疗的核心,对患者的个人史来说甚至它比基因学的解释更重要。
根据Gill所提出的,Freud的治疗技术显示了两个不同的方面:移情可以被看作是对回忆的一种阻抗——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收获是因为动员了这些被拒绝的记忆和情感。另一方面,移情被看作是患者的潜意识愿望想要在分析关系中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目标是修通这些潜意识地愿望,这些愿望是来自于孩提时的、在治疗时刻中复苏的、与分析师密切相关的。
从这个观点看,在潜意识的内部戏剧的现实化过程中,移情变得明显起来。因此,在移情中,对其进行分析并不是目的,而是移情本身变成了神经症的现实化。
对移情修通得越多并最终解决,潜在的神经症性主题的病理作用就越少,就越会转向更健康的解决方法——这是一个Freud自己已经清楚看到的非常重要的观点。
基于上面所提到的,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即对移情的分析已经越来越成为分析过程中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可以被看作是通往患者潜意识之门的主要钥匙,它将这些潜意识以非常情感的方式带入到与分析师的关系中,这种情感的方式与纯粹的理智化非常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仅仅着眼于患者的过去就会产生理智化的结果。当分析师聆听患者时,他就不断了解到那些材料的相关关系——无论患者说什么都具有一些潜在意义,这些意义是和分析关系相关的。

Copyright © 2008- 德中心理咨询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