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心理咨询机构”,“石家庄心理咨询中心”,“石家庄心理咨询”,“石家庄心理医生”,“石家庄心理”,“石家庄德中心理”,“石家庄心理实习”,“石家庄心理督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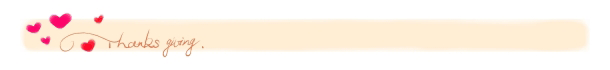
移情关系中存在和死亡感的分析方法
作者:Thomas H. Ogden
译:劳申玥
Copyright ©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1995
前言
移情-反移情中的存在感(aliveness)或死亡感(deadness),反映了分析体验中挑战性的方面,可能也是一个分析过程中此时此刻状态评估的重要信号。这篇论文中,作者讨论了四个临床主题,用以描述移情反移情关系中出现存在感和死亡感的重要性。高亮标记的部分,是指在一个分析关键点上,从反移情角度处理存在感和死亡感所扮演的防御性和表达性角色,并以此来解释移情反应。病人内在客体世界中所体验到的存在感和死亡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客体关系的特质,可从中得到检验。
现在我们要狩猎第三只老虎,但是如同
其他那些一样,它也是我梦中的构建,一个词语的组合,
而不是一只超越了所有神话故事的有血有肉的老虎,行走在大地上。
我很清楚这些,但仍然有某种力量驱使着我,
在这模糊的、无意义以及焦虑的谜题中,
我将继续穿越永恒的时间去追寻
这不存在于诗歌中的,另一只老虎。
——《另一只老虎》J. L.博尔赫斯, 1960.
近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对我来说,移情关系中体验到的存在感和死亡感可能是分析过程中此时此刻状态评估最重要的信号。在这四个临床主题的讨论中,我将探讨一个分析技术的基本元素,关于分析师使用他的反移情体验来处理分析中的存在感和死亡感,以及这些体验对病人呈现或掩盖他的内部客体世界和客体关系的作用。从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会更关注这样的问题:双方最近一次感到分析是有活力的是什么时候;是否有被掩盖的活力,因为害怕意识到它所昭示的内涵,而不能被分析师或分析者所承认;掩盖分析中的无力感的替代症状是什么,比如躁狂性的兴奋,反常的愉悦,歇斯底里的表现和行动,假装模式(as-if constructions),依赖分析师等等。
我提出的观点很大部分是基于温尼科特关于“我们所在之处”的设想(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第三个体验空间[1951]),以及在分析中如何产生这样一个“空间”(主体间性的状态)。我也很大程度借鉴了比昂的概念,分析师/母亲保持活力,某种意义上是给分析者/婴儿带来了生命,分析者/婴儿通过成功内化了投射性认同,获得投射性的自我。Symington (1983) 和Coltart(1986)的关于分析师的自由联想的探讨,代表了对温尼科特和比昂的分析技术的重要应用方向。Green (1983)对早期无意识状态下对抑郁母亲的内化,所带来的死亡感的分析性理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年来关于分析师的“真实”已有很多论述,比如他源于自己的体验,自发自由地回应分析者的能力,而不是被僵化模仿的“分析式中立”所牵制。客观地说,我自己在分析工作中很少直接地与病人讨论反移情。但是,当我将自己置于分析师角色时,反移情已经不言而喻地表现在我的工作方式中,比如制定分析框架,我的语气措辞,解释的内容以及其他干预,费用也是对应于缓解张力的一种象征行为,等等。
在探讨一些观点之前,我得先探讨一下技术问题,关于如何定义、言语化以及解释分析中的存在感和死亡感。我相信每一种精神病理学的症状都是一种特定的形式,表现了个体要充分成为一个人的能力局限。从这个角度看,分析的目标不仅仅是揭露无意识的内心冲突、减少症状,以及增长个人能力。虽然一个人充分活着的感觉和上述这些方面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我相信存在感仍是一种高于那些方面的特质,并且以它应有的价值看做是分析体验中的一部分。
这篇论文是着眼于临床的。我不会去定义心理学意义上的存在感和死亡感,也不会去阐述我们如何测量它们,或者什么程度上,一个分析体验称得上具有存在感或死亡感的特质。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探讨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去讨论某些临床情境,其中我认为是以这些体验特质为主,并且希望通过这些描述,它们会自己传达出一些分析师和分析者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在四种关于存在感和死亡感的精神症状的临床讨论中,反移情体验被用来创造分析内容,比如澄清、标记、理解和解释移情反移情关系中的张力。
====================================================================
I:失去存在感的N女士
在第一个临床案例中,我将例举一个分析片段,其中病人的死亡感在最初不能被言说,于是变成一种死气沉沉的分析体验而被掩埋起来。
N女士是个非常成功的公益活动领袖,她开始进行分析是由于她感到紧张、弥漫性的焦虑,认为自己的生活有些地方很不对劲,但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在最初几次面谈中,她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空虚、无效或停滞的感觉。她说她感到说不出话来,那完全不是她的风格。
*注:我用“反移情”
这个词表示移情关系中分析师这部分的体验。“移情关系”指分析师和分析者双方无意识的主体间结构。我不认为移情和反移情是一方对另一方回应产生的独立事物,而是,我把这些看作分析师和分析者各自体验到的完整主体间结构。
在第一年,也就是分析进程的一半期间,很多方面都显示这是个令人满意的开始。病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她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和人们(包括我)保持一个良好的心理距离。焦虑感也有所下降,可以从病人在躺椅上不再那么僵硬的姿势反映出来。(几乎一年来,N女士躺在躺椅上时一直把她的手盖在胃部,而在会谈最后阶段,病人可以直接地从躺椅坐起,轻快地看也不看我就离开房间。)病人的语言在最初很严肃而且经常用书面语,在第一年的工作后她的讲话方式变得更自然了。但是经过这个阶段,对于分析对她是否有任何“真实的价值”,病人仍然抱有疑虑。N女士认为对于她焦虑的来源,或者生活中哪里不对劲的感觉,并没有发展出更深的理解。
在第二年工作的前半段,我逐渐意识到病人的模式,讲着看似反省的话语,但那些并不能发展成带来深层理解的内容。N女士会详细描述她生活中的事件,但完全不清楚这些冗长描述的重点是什么。同时,我会对病人说,她一定很担心,如果她帮我理解到她所说的重点是什么,我就会对她了解得太多了。
我发现我对病人越来越没有好奇心,这很困扰我,这种感觉就好像我的头脑失去了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经验到某种像幽闭恐惧似的感受,有时为了抵抗这种焦虑感,我不由自主地数着时间捱到治疗结束。有时候,我会幻想索性跟病人说我不舒服,提早结束这次分析。还有时我靠数自己一分钟的脉搏数来“捱时间”。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我数心跳这有什么奇怪的,但事实上在其他病人那里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伴随着这个动作一起产生的那些想法、感觉和感受,它们给我的感觉并不是“分析数据”,而是一种无形的、私人的背景体验。
在那以后的几周,我渐渐能够把我的脉搏,连同那些综合的感觉感受一起,当做“分析的对象”来处理,比如作为我和病人无意识建构的一种反应,或者更确切说是“主体间分析性的第三方”。我已经在近期发表的论文中谈过关于“主体间分析性的第三方”(或“分析性的第三方”)的概念,大致概括一下,主体间分析性的第三方是指分析师和分析者无意识互相作用产生的第三个主体,同时,双方经由创造分析性的第三方而成为分析师和分析者。(分析性的第三方建立的过程中没有分析师、分析者,也没有所谓的分析。)
新的主体(分析性的第三方)处于分析师和分析者个人主体的对立面。主体间分析性的第三方不是构想出来的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一种不断演变的经验,随着分析双方创造出更多理解而变化流动。
分析性的第三方通过分析师和分析者个体的人格系统被经验到,但对双方来说并非同样的体验。分析性的第三方的建立,反映了分析情境的不对称,由分析师和分析者所扮演角色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分析情境。但分析者的无意识体验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分析者(过去和现在)的体验,在分析谈话中被当做双方主要的(即使称不上唯一的)话题。
我开始能够连接我握着自己手腕(数脉搏的行为)的感觉,现在我怀疑那是我想要感受人类的温暖,确认自己是活着的健康的,这是我安抚自己的努力。这个领悟对于我和N女士工作在很多方面带来了更深的理解。我被病人超过18个月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跟我讲些看似无意义的故事而触动,病人提供这些故事,其中隐含着无意识的愿望,希望我去找到(或创造出)这些故事的意义,然后可以创造病人生活的意义(一种凝聚性的、指导性的、有价值的、真实的感觉)。之前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想要装病来逃避这停滞的治疗,但是我没有理解到,这个“借口”也反映了一个无意识的想象,即我因为长时间处于这种缺乏生命力的分析中,正在变得虚弱。通过这个想法,以及其他几条相似的想法和感觉(联系到分析第三方中我的体验),我开始能够理解病人弥散的焦虑感,以及她被一些说不出的糟糕的东西所困扰的感觉。
我对N女士说,我现在比较理解她为什么会用那种令我们俩都很迷惑的方式来讲她生活中一堆细节。我说我感觉她已经放弃了为自己创造生活的能力,于是她给了我这些碎片希望我从中为她创造一种生活。病人说她工作和在家的生活都完全是在为别人组织活动,而没有为自己做任何事。现在看起来她是在用别人的生活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包括她的员工、丈夫、佣人和她的两个孩子)来代替她创造自己生活的能力。
之后病人说到,很长时间以来她都在想我桌上的纸镇是另一个病人给我的礼物。她说她没有提到过她注意到这个东西,但她一直都希望那是她送给我的就好了。直到那时候她才意识到,她不是在幻想自己送了个礼物给我,而是幻想那个礼物是她送的。她不能想象自己是个可以选择——或某种程度上说——
创造一个礼物给我的人,所以她幻想自己成为送我礼物的那个人。这时候我没有做解释,我想,这个想法之下潜在的幻想是,她不可能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所以她唯一的可能是从别人那偷来生活。看来我不应该抢走病人创造自己生活(在分析中创造对自己的诠释)的机会,而她现在可以开始尝试了。
几个月后,N女士报告了一个梦,她在一个厨房的橱柜里,但那不是她自己的厨房。似乎是她变成那种木柜子的方块形状被“塞到橱柜里”。报告这个梦的同时,病人还告诉我,她一个朋友因5岁女儿的死而一直遭受内心的痛苦。这个朋友的孩子是死于病人开始做分析之前,因为保姆疏忽发生意外。
告诉我这个梦之后,N女士沉默了。这种沉默明显不同于过去掩盖在连篇废话下的模糊的感觉。几分钟后,我对N女士说,我认为她是在描述缺乏自己的形状的感觉。我继续说到她朋友的痛苦,虽然很糟糕,但这却是病人恐怕自己承受不起的人类情感。我告诉她,虽然她从未直说,我感觉她是害怕可能自己永远不会有任何感觉,甚至包括失去孩子的那种痛苦。
N女士用我几乎要听不见的微弱声音说到,很长时间以来她害怕的这一点令她感到很羞耻。很多次她整夜睡不着,担心如果她的孩子要死了她都不能感到悲伤,这会是最她最无法忍受的失败,换作其他母亲也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她说她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像她希望的那样去陪伴和爱孩子。于是,现在她知道自己很严重地忽视了他们,孩子们也遭受了很多。在这次治疗最后几分钟里,病人再一次沉默了。
总结一下,刚才讨论的分析片段代表一个过程的开始,病人的死亡感体验(没有悲伤的能力,以及提到她朋友女儿的死)从一种无法进行思考的状态转化出来(病人和我都切实感觉到一种死气沉沉的非言语的感觉),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对死亡感言语化的体验。一个主体间分析空间开始被建立,在其中死亡感能够被体验、被看到、被经历以及被我们两个言说。死亡已经成为一种感觉,而不是一个事实。
=======================
II:与D先生的相遇
在第二个临床讨论中,我将结合当病人无意识地坚持要分析师作为他精神生活及希望来源的情况,由此提出一个技术性的挑战,即分析性的相遇。
D先生,在开始几次会谈中告诉我说他已经进行过6次分析,每次都是“被终止”分析。最近一次单方面的终止分析是发生在D先生第一次来见我的3个月前,
这个病人的举止和讲话方式带着一种傲慢、冷淡又自我中心的感觉。与此同时,这种举止又显得很脆弱,明显说明病人带有优越感的语调,是在掩饰着害怕、无价值和绝望的感觉。
D先生告诉我,如果要他在前几次面谈后继续往下走,我必须理解他在每次分析中永远不会是先开口说话的那个人。他解释说如果我想要“等他先开口”,这次分析就要在完全的沉默里度过了。过去他已经太多次用这种方式浪费了时间和金钱,希望我不要再重复这种方式来和他工作。他又补充说,如果我要问他不能先开口背后的“恐惧和焦虑”,那也是浪费我的时间:“毕竟,我要是回答那类问题就相当于我开始进行自我分析了——你知道我不会的”。
D先生的自我介绍引起了我的好奇,并且激起了我的竞争感。他已经发起了挑战,我就得证明我比之前六位分析师更胜任更敏锐。在前几个小节中,我也怕自己无意识地扮演了“求婚者”角色,有一种同性间施虐受虐情境的幻想正在移情关系中显现。与此同时,我发现当我进入一场想象的竞争游戏,这使我免于当前遭遇到的强烈蔑视和恨意的严峻挑战。而且,D先生狂妄地控制分析师的工作方式,我的自恋/竞争的幻想也使我免于陷入他用这种方法编织的网。我想象如果我们要一起工作,将有长期的隔阂等着我们。
我对D先生说,我认为他想象中与我的分析工作会是一方或双方残酷地对待对方——直到一个人受不了。我还说我没有兴趣虐待他,也没兴趣被他虐待或参与他的自虐游戏。这番话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关于我将如何工作的分析框架的声明。我同意每次由我先说话,但是只有我认为我有话要说的时候才这样做。我还说在一小节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我的体验转化为语言,但我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我在“等他先开口”。
我说话的时候D先生安静地坐着,看起来放松多了。我欣慰于,我能够对D先生说些什么,既不是出于施虐性的攻击,也不是我们谁的妥协。对我来说,这也不是一种躁狂的兴奋或者拒绝幻想中的竞争游戏。
在与D先生每次会谈的开始,我会尝试表达此刻我和他在一起的感觉。我(默默地)作出假设,移情关系中关于虐待和兴奋(竞争)的想象和感受,表明了对抗内在死亡感的防御方式,这种死亡感也表现为D先生感到他没什么可以拿来开始一次分析小节(开始述说他的故事)。每次见面只能由我给分析带来生命力(创造历程)。几乎每次都是我先开始,就好像我在给病人和分析做人工呼吸来使生命力复苏。我选择不直接告诉D
先生这个想法,因为不想贬低他或过早地涉及移情关系中同性恋方面的问题。
那时候,分析开始时我对D先生说的话变得机械而重复,为了不掉入他所带来的更深的无力感中,我努力地无视这些陈词滥调。在分析工作早期的一次会谈中,我告诉D先生我发现自己想要诱惑他信任我。我说我知道这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破坏我们的关系,因为任何事情上我“赢”了,都会被我们经验为一种盗窃行为,使我们比现在已有的关系更疏远。沉默了几分钟后,D先生说他一直很关注防盗问题:家里用的防盗铃,车上的防盗机关,办公室的保险柜等等。虽然没有明说,但这是对我刚才所说的回应。尽管病人用这种方式提供信息,但这次的感觉是极度地紧张僵持,好像随时会关系破裂。感觉就好像分析中已经没有人在维护关系。
在分析到6个月的一次会谈中,我认为当时看到了D先生眼睛里含着泪,我仔细看又不确定是不是看错了。(那时候D先生不愿意用躺椅所以我们是面对面。)我告诉了D先生这一点,问他是不是眼睛里有眼泪,我认为这反映了我们所处状态中的悲伤。(我记得D先生几个月前告诉过我,他很感激前任分析师坦诚地跟他讲,如果她无谓地坚持这种不会有进展的分析,这样不会帮到他。这一点使我想起最近一个亲戚跟我讲到“生命的意志”,实际上医生的原则是,如果病人已经失去了真实的生命,他们不会去维持一个空洞的假象。)
D先生沉默地坐了几分钟,他说这让他有所触动,然后又回到他的沉默里。大约5分钟后,我说我认为刚才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定是反映了他的一些体验。我感到悲伤,其中有部分毫无疑问是我自己的,是我感觉到和他相处带来的极度的孤独感。我在代替他去感觉一些东西。我说,过去我努力和他讨论这些,但他的回应总是让我觉得自己要么疯了要么很傻。我说要不是我对自己的能力还有些自信,能够去区分哪些感觉是真的,我可能会因为自己这么全然地卷入而压力很大。我告诉他说,如果在他生命中某些重要的方面,他可以有能力区分自己的体验和感觉中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而不感到那种压力,我会很惊喜。从我和他相处的体验来看,他努力维护着自己真正的所思所闻,一定是有很强烈被评判的感觉。
但病人几乎完全无视我刚刚说的,转而提起我在第一次会谈中用了“虐待”一词。那个词是最贴切的,在这几个月的分析中“也许是唯一贴切的词”。他说他从没有像小孩一样被打或被虐待,但他感到隐隐约约被粗暴地对待,如果实际上确实有些不寻常的事发生了,但他还是无法述说,因为他都不确定发生了什么。D先生说他不打算讲他的童年,因为太正常了——“在以前的分析师那里我已经讲过一百遍了,但是其中没什么可以让我在真人秀里博人眼球的。”
这次交流是我和D先生关系最近的一次。在之后的几周,他明显变得对我和分析很敌对、贬低。我指出这个事实,在上述这次会谈后,他戏剧化地开始攻击我和我们之间互相交流的努力。比如说,他对我把这些“昂贵的时间”称为“工作”表达了强烈的鄙视。我对D先生说之前他还提到我的另外一个措辞“虐待”。我认为,我用了那样的词来描述他的感觉,使他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些事情开始变得强烈而危险,开始失去控制。我说刚才发生的表面上看来是他在攻击我,但对我来说更像是,通过激怒我甩了他来保护我。我又说,我猜测如果我没有马上结束我们的分析,他也会退出,因为他害怕自己无止境地攻击我,而他想要保护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结束分析。D先生没有结束分析,但是几乎六个月的时间,他都在会谈开始时转过椅子背对着我。我猜想他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眼睛。那个阶段的工作中,他甚至比开始几个月说的还少。
在上面讨论的这些分析中,D先生在幻想中把我看做是他生命和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他攻击我,而且天真地想象我会在他的粗暴攻击下保护好他和我自己,我仍然替他表达,替他感受(通过每次会谈由我先开始,通过作为一个容器,投射性认同他的孤独和悲伤。)切入病人的施虐受虐方面的问题对我保持和病人的连接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病人开始能够体验对他自己的悲伤和同情,他把这些投射给我,又通过我而体验到。
=======================
III:督导-模仿的“完美分析”
在临床医生来找我督导讨论个案时,我不仅会问分析师他们说了什么,也会问分析师在那个时刻的想法、感觉和感受。我会问分析师他案例记录中的这部分内容,并在我们的督导会谈中谈论。另外,我会建议分析师应该对所有的会谈做案例记录,包括病人缺席的时候。
我工作的假设是基于,当病人身体缺席会对分析师和分析过程创造一种特别的心理效果,于是即使病人缺席,但分析过程仍然在继续。通过这种方式,病人的缺席被转化成分析的素材,由此可以充分地体验、与它共处、言语化、被理解以及成为分析谈话的一部分。
用这种方式运用案例记录,分析师可以言语化并说出他与病人工作的体验,不论表面上看来多么的与病人无关,分析师的幻想、身体感受、反思、白日梦等等能得以呈现。我并不“坚持要求”找我督导必须讨论这部分的体验,因为一些分析师在最初能力上还达不到参与这种水平的讨论。另外,找我督导的分析师并不总是能得心应手地与我一起对这部分工作。不过,我发现随着督导关系的展开,被督导者通常能够开始发展这种能力,可以在他们的心理咨询工作中利用这部分的体验。我也发现如果之前没有进行过个人分析,很少有治疗师可以投入这种形式的督导。当病人缺席(并不是指“分析已经完成”),如果他可以在工作中利用那些占据着他的日常隐微的想法、感觉和感受,这对分析师能力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作用。
从分析技术的主要观点来看,关注和运用分析师那些看似与病人无关的个人表述,与我们过往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人格防御背道而驰。放下对这些人格防御的依赖,就好像“撕开皮肤”,使我们对刺激的保护屏障变弱,而无法维护内部与外部、适度感受与过度刺激、理智与疯狂之间的边界。
我现在要谈的这段分析工作发生在一个分析师和我的督导过程中,他每周一次来见我,进行了约1年。这个分析师带着对分析很大的失望开始我们的工作。被分析者C博士是一位全科病房的住院医师,在学校里读过精神分析,上医学院并度过实习期。他对“分析设置”有很强烈的执着而且严格遵守,尽管从一开始他就抱怨“游戏规则”太死板,比如被分析者应该为取消的会谈买单,在分析师“允许”时分析者才可以度假,要求服从“基本规则”等等。(关于这些费用约定上的抗议,其实分析师没有说过这些“规则”。)
C博士对于他来做分析的理由很模糊:他认为作为一个全科医生,他应该将“了解自己”作为他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他不愿承认因为正经历心理痛苦才来寻求帮助的观念,可能表明了他想象中的服从行为,而那是病人在分析一开始不能忍受的。这个分析者每次都很准时,配合地“自由联想”,报告了一堆事情,梦、童年记忆、性幻想、最近工作的事、婚姻及抚养孩子的困难和压力。其中有病人对感到羞耻的秘密行为的忏悔,比如看色情杂志手淫,2次在医学院的实验报告里作假之类的。
总之,经过早期几次的分析,分析师F医生觉得这个病人无聊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很不适应。感觉就好像这位病人想要模仿他想象中“完美分析”是怎么进行的。
这就要求F医生有相当的忍耐力,才能不在分析中对报告内容做诠释,比如对“貌似征求移情诠释”的梦做诠释。在督导咨询中,F医生讨论了他想到的可能的诠释,但他选择没有马上说出来。在我看来,这些诠释也是对“深刻”移情诠释的模仿,并且一定程度上F医生努力呈现这些来创造他自己幻想的“完美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分析师感到很想要惩罚分析者,甚至轻蔑地评论病人连篇废话中的空洞感。督导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洞察,包括一个关键性的重点,F医生没有进入这个空洞的谈话(懈怠),并且很重要的是,同时分析师也没有发挥自己的能力去体会那些升起的想法、感觉、感受。对病人没有什么解释或反应,就会被病人排斥或使分析变得停滞。F医生这方面应投入大量心理上的努力,而不要变得机械化、隔离,或者是模仿我、模仿一个理想化的分析。
F医生开始有了他自己的风格来做案例记录,其中他可以从完整的分析体验中捕捉到一些东西,包括他自己经验中的细节。我认为这是分析师从“整体情境”的角度,努力聚焦于移情关系中反移情的部分。换句话说,不单纯是移情,而是移情-反移情组成了分析的空间,心理意义在其中得以形成。
F医生会在我们每周的督导咨询中报告他的分析过程,要将F医生的想法感觉和病人的做一一对应的分析,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困难。那时,我们会互相提出假设性的理解,关于F医生的体验和治疗中发生的事之间的关系。通常,F医生简要记录下来那些遐想,随后我们就会聆听到这些材料在我们之间回荡的回音。有时我们会在谈话中回头引用那些F医生几周前或几个月前报告的遐想。
开头几个月的分析中,F医生经常提到对他即将到来的休假充满期待,或者最近下午茶时间逛了有趣的店铺和书店。这些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一般逃避现实的幻想,而是,这里每句话都是对分析中某个特定时刻的回应。有一次,F医生关于度假的白日梦有点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似乎是对应着分析中那种粉饰出来的自然。那个病人不想要一个真实的分析;他防御性地渴望一个完美分析。换句话说,分析师无意识地期待自己轻易地创造出一个分析,而不用卷入他和另一个人真实的相遇,包括那些必然要承受的由于人际间疏忽、误解等等引起的焦虑。
尽管F医生经常从病人那里收到像预先设置好的回应,他还是希望自己内在有能力保持活跃的好奇心,能够对分析互动中发生的事自发地提出疑问、解释。F医生并没有把“分析礼仪”
理解为恐惧,而是看做病人的冒犯和反对。比如,有次病人表示他想要F医生给他建议,但是马上又说他知道F医生是不可以给他建议的。最后什么建议也没给,却开始讨论病人是用一种想象的规则(全能感的产物和投射)来阻挡他自己去感觉和思考他自己和F医生之间发生的个人化的、特殊的、无法预测的体验。
当F医生感到对病人说的内容有点好奇时,哪怕是次要的问题他也会让病人再深入说点细节。举个例子,有次病人随口说到前个晚上去了个不错的餐厅,F医生就问病人餐厅的名字。现在比较清楚可以看到,遗漏细节(餐厅名字)很可能是一种诱惑或拒绝分析师的方式(病人对分析过程的好奇心和排斥感的投射)。总之,那时F医生对他感到好奇的部分决定再问些细节(可能更确切说是意识到自己在问),但是没有去探索这个遗漏的细节引起的诱惑效果。(Coltart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如果还没分析过病人想要逗笑分析师的有意无意的动机,要留意观察自己允许被病人的笑话逗笑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F医生想要保留分析中自发性的和“头脑自由”的时刻,但他却一点也没有用随意自然的态度来维持分析框架——治疗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候诊室和咨询室里没有随意的交谈;在这个小心谨慎的案例中,建议、保证、劝导诸如此类的也不比其他的分析中要多。
在第一年分析的大部分时候,F医生感觉他的力气几乎全部用在维持他自由联想的能力以及和我讨论这些念头上。第二年初,病人开始有所不同,表现在能够用他自己观点说话,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套、刻板、模仿。然而,这些变化对F医生来说脆弱而短暂。
在这段时期的分析中,F医生在我们的督导中报告了一个分析小节,那次病人在面谈开头的几分钟里没说一句话。F医生告诉我说,在这段沉默的时间里,他在想我会去夏威夷过圣诞节假期。他想知道我会不会在旅行中带上红绿彩纸包装的圣诞礼物。他想象在夏威夷交换圣诞礼物多奇怪啊,还想到我妻子会送我羊毛衫作为圣诞礼物。我给的解释是,F医生想表达对我们督导中讨论过的一些观点的怀疑,特别是我着重强调F医生工作中创造性和自发性的能力。
讨论F医生关于我度假的白日梦时,我对F医生说,我认为他是把我想成了正在玩一种自我欺骗的把戏,好像我把圣诞节当做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挖出来挪到另一个地方,就像一个人可以把一棵植物从院子一边移到另一边,而对它的感觉却没有不同。这个白日梦的感觉就像在说,圣诞节已经完全成为了我的模式,而我对这个死板的形式没有觉知。这个想法反映了F医生的失望,以及把我看做对自己的机械化缺乏自我反思,某种程度上也是带有竞争的快感。
F医生说的似乎是针对我们两个,“关于真实、可靠、真诚、自发性等等,Ogden都说的很好听,但是落到实践上,可能他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F医生和我讨论了我出于自发性地设置收费的方式给他造成了各种困扰:他发现开始想要“训练自己”变得更自发。更糟的是,他可能有种无意识的感觉,“实现自发性”是在模仿我。通过讨论这个圣诞节的白日梦,结果是F医生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病人有时也在治疗中承受类似的负担。这几个月来,C博士说他感到有种内在的压力,要在分析中“保持状态”,也就是要对F医生来说够有趣。在这个点上,C博士的话总算带有了分析的意味(成为一个“分析的对象”),变得可以被言语化、反思以及解释。F医生感到他现在更加理解病人内在要“保持状态”的压力反映了病人没有意识到的观念,他只有像F医生那样学会思考、感受、说话和表现,对F医生来说他才是活生生的。这使得病人处于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也就是要显得生动和有趣。矛盾的是,对C博士来说,变得生动有趣就相当于变成(理想化状态的)F医生。
在几次成功的分析那个阶段,F医生对被分析者感到分析中要“保持状态”有压力的原因给出了他的理解。这个解释以及F医生的自我反思,促进了创造出一个分析中的心理空间,在其中病人和分析师能够持续产生想法、感觉和感受,而不会觉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和模版需要他们去模仿。
在刚才描述的临床片段中,最重要的是分析师可以有他自己的、独立于我的想法(通过F医生在他的圣诞节白日梦里对我的批判而得以言语化)。只有当F医生意识到,自己原有的思想被抑制是因为害怕承认自己对我有理想化,他才能重获完整的自由联想能力。如同在圣诞节白日梦里描述的那样,对这个防御性历程的言语化和理解,成为了分析病人的基础,即他徒劳地通过(幻想)成为一个完美的病人来克服他的死亡感,也就是说,防御性地成为一个理想病人。
================
IV:人性的连结
最后一个临床片段我会聚焦于“竞争”的问题,是由人格中病理性自闭的部分引起的,表现为一种无生命力的状态。在成年患者的分析中,人格的自闭部分通常一开始完全看不出来。这是S女士的分析案例。在分析开始几次面谈中,S女士谈了她“把生活处理好”的困难。无法集中注意力使她没能大学毕业,她的婚姻也是一团乱麻,感觉自己正处于疯狂的边缘。
分析的前八年每周五次,我没法在论文里记叙这个分析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如果要大致概括这些年的工作结果,可以说,虽然病人适应这个世界的能力已有很大不同(例如,她能够大学毕业而且维持着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是病人与别人建立关系的能力还是很有限。S女士和她丈夫分开不同的卧室睡,偶尔会有那种按病人的说法“机械的性爱”。看来还需要至少五年分析,病人才能意识到她只是在“管理”她的三个孩子,就好像她是个“日托班”的工作人员,而她单独对每一个孩子的感情几乎没有。她的朋友关系也很浅,直到第七年分析末尾她才开始意识到她的生命中缺乏爱的联结。
在分析关系中,我一再地惊讶(在其他病人那里几乎没有这样),她竟然如此严重地无法对我表达温暖,也无法从我这里感受到温暖。并不是说S女士不依赖我,周末的间断、休假(她自己的、我的)、每一小节结束,都令她苦恼,于是会频繁地拨打电话答录机只为了听听我的声音(但她不留言)。但是,S女士不觉得她的依赖是一种人际间的依恋,而是一种她深恶痛绝的上瘾:“瘾君子并不爱海洛因。她渴望得到它并不意味着她爱它,或对它有任何感情”。病人在她的隔离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不为所动,而且似乎认为“对人性的弱点免疫”比生命中任何事情都更有价值。这种“不为所动”的特质反映在她的厌食症里,她靠水果、谷物和蔬菜维生,在生活里安排严格锻炼内容,包括马拉松慢跑、健身房单车。病人每天至少进行三小时苛刻的锻炼,如果运动进度被干扰(比如生病或外出),她会非常焦虑,有两次甚至惊恐发作。
在分析开始,S女士对食物、性爱、思想、艺术或任何东西都没有欲望。对她来说体重才是最重要的——通过保持一个特定的体重(她生理上可以承受的、不至于得病的最低限度),她由此获得一种力量感,好像可以控制任何发生在她内心或外部的事情。
如果说病人在分析中总是麻木没有感觉也不对。S女士经常对我有激烈的愤怒,她称之为“憎恨”。不过她的愤怒似乎从来不是人性化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好像她的愤怒跟我没什么关系。这种憎恨似乎也不是病人自己制造的,当她对我的完全掌控和所有权受到挑战时,它更像是一种盲目的、反应性的感觉,几乎抽搐颤抖起来。因为正好是我出现在那里,于是就成了她愤怒的对象。S女士对我的指责总是和她投射性幻想里我的全能有关:她觉得我可以轻易地给她所需要的,如果我想的话,但我就是不给她。
她一心讨伐我要获得我无所不能的力量,除此以外,她对我几乎没有兴趣。我很难接受,除了刚才说到的幻想主题以外,我对这个病人怎么会这么没有价值。几年来我坚持着一个假设,S女士默默地爱着我(尽管用一种原始的方式),对我有关注,对我这个人有一些了解,但是她固执地拒绝承认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基于病人强烈地依赖我的感觉,以及我也关注她、对她感兴趣。有时我认为是由于病人害怕接触到她内部外部的世界而失去控制,所以不愿承认与我有人性化的接触。她会回应说,虽然我说的是对的,但她对我或对任何人都没有感觉到情感、爱、温暖,或哪怕只是关注。我用许多说法来解释病人这种态度的防御作用,但没有看出来任何情感上的转变。(这些解释对病人和我来说显得越来越老套。)
可能是病人对我父亲去世的反应,使我开始放下病人默默地爱着我或关注我的观点。由于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在第八年的分析中),使我开始觉得,S女士所表现出来的不能与人链接的特质,和我与其他病人之间碰到的出于对爱恨的恐惧而防御,两者是非常不同的。得知我父亲去世的坏消息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病人和被督导者们说,我家里有人去世了,我得取消几天的面谈预约。我告诉他们,等我可以恢复工作,我会打电话通知。当我跟S女士说这事的时候,她安静地接受了,但是马上问我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工作。我说不知道,等我确定了会告诉她。
我回来后的第一次面谈中,S女士说她感到“很遗憾我家有人去世”。她的语气里毫无疑问带着气愤,因为她重音落在“有人”这个词上。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说不知道是谁去世了这让她有很强烈的感觉,还说我打电话给她却不告诉她这个信息很过分。她说我肯定对其他病人都说了我家谁去世。通过这次交流,我获得了一个确认,这严重地扰动了我,是我接近十年都不想承认的:S女士对我作为一个人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她需要努力地占据我、控制我,以此来保护她自己。
在此刻,我开始回忆起听到父亲的死讯后马上打电话给S女士时的感觉。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感觉,我对她说话时努力控制语气、收住眼泪。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她其实没听出来。她怎么可能感觉不到,那时是我们两个有紧密连接的时刻?但是,她显然只觉得那时她的全能感又一次被挫败。
我能听到自己说话的语气,从S女士那里感觉到一种无动于衷的疏离感。同时我也第一次从这种声音里听到了某些别的东西。那是一个冷淡的伴侣的语气。我明白到,S女士所生活的世界里,人们互相隐瞒。
在那个节点上,我发现我才刚刚开始理解S女士和我的关系,那是我之前没抓到的重点。这个新的领悟并不能使我免于在S女士那里领教她的冰冷无情,我知道这冰冷无情反映了她人格中自闭和偏执分裂的部分;同时也不能掩盖一个确认,在这强大的自闭、偏执分裂防御的另一面就是人类爱的能力。在这个点上,通过回顾我看到,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自己缺乏对S女士的同情,以及她试图安慰我的方式就像我妻子,这些使我看不到一个事实,她看似缺乏同情心其实是表现了她人格中强大、共存的两方面的复杂互动。她对我有关注,而且当她的爱无法被我了解,她感到非常沮丧(比如反映在我拒绝让她安慰我)。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S女士无法像一般人那样生活,而是处于一个机械的、全能化的世界中:(1)与“自闭状态”和“自闭客体”有关(例如用机械的、自给自足的方式锻炼和节食,参与到感官世界。)以及(2)占据我、寄生般地活在我身上的偏执分裂幻想。
我已经不能忍受、也无法阐述解释,在生和死之间我们关系中模糊不清的互动影响(例如病人的人格中,抑郁、偏执分裂和类自闭状态几种维度的共存)。S女士既是爱我的,但也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对她有感情(我渐渐更充分地从自己的体验中辨认出来,那感觉就像一个冷淡的伴侣),但不会允许自己对这样一个明显缺乏人类情感的人感觉温暖或哪怕是同情(比如从她对待丈夫、孩子的态度,以及对我的反应,特别是我父亲去世的事)。
在我刚描述的这节分析稍后,我对S女士说,对我们的关系我低估了两件事:关系中感情的分量以及我们之间毫无关系的程度。当我对这两方面视而不见时,我就无法完全地理解她是谁以及我们是谁。我还说,我以为我们之间可能完全没有情感连结的想法,对我们的互相了解是一种贬低,不过那其中还是有值得重视的动力。
S女士回应说我以前从没对她那样说话。之前她总觉得我有时就像她一样冷酷,她可以从我的语气中听出那种冷若冰霜。而现在她探查不到那种冷酷了。S女士继续说道,她无法相信那些冰冻已经融化了,但至少此刻起它们不再决定着我们之间的一切。
我把这理解为病人达到了一个阶段,能够接受我对她的理解,并且从中获得信任的感觉,而这是她以前从未能做到的,要么马上反击,要么更通常的反应是退行到自闭自足的状态或全能化的偏执分裂幻想中。我的诠释既没有否定她情感上的死亡(出于自我保护的偏执分裂和自闭模式),也没有否定她与我产生人性连结的能力正在增长(尽管她不愿轻易承认)。
===================
结语
报告这四个临床讨论是为了描绘一种工作方式,其中存在感和死亡感通过主体间分析性的第三方得以产生和被经验到。在每个临床情境的描述中都存在着无意识呈现的、强烈影响着分析,却避而不谈的内容,而分析师试图从中创造出分析的意义(“分析的对象”)。正是通过分析师运用他的遐想,他的隐微的想法、感觉和感受(经常看起来和病人无关),那些特殊的、可诉说的意义被创造出来,并最终运用在诠释的过程中。所描述的四个分析,移情-反移情关系中产生了存在感和死亡感的特质,构成了重要的主体间结构,反映了被分析者病理性的内部客体世界的核心本质。

Copyright © 2008- 德中心理咨询中心